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用儿戏般的计算公式给全球贸易体系“埋雷”
- 国际
- 2025-04-05 17:40:05
- 6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加征“对等关税”,引发国际社会哗然。加征“对等关税”的理论基础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对等关税计算公式”。USTR声称通过科学方法估算了各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此确定对等税率。然而,这一计算方法在理论依据、数据应用和政策执行层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其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据此采取的错误贸易政策将通过单边高关税政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势必引发各国报复,威胁战后几代人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贸易秩序。

特朗普“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理论与实践谬误
USTR提出对等关税计算公式为:Δτi=(xi-mi)/(ε*φ*mi)。其中,Δτi表示美国对国家i征收的对等关税税率,xi为美国对国家i的出口总额,mi为从国家i的进口总额,ε为进口价格弹性,φ为关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xi-mi)表示双边贸易差额。
USTR声称,该公式通过引入价格弹性和关税传递率,科学计算了对等关税税率。然而,这一公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存在多重谬误。
首先,该模型的设计过于简化和理想化。从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其公式虽然引入了价格弹性(ε)和关税传递率(φ),试图基于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弹性理论和关税传递机制来估算关税对进口额的影响,但这种方法在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现实时显得力不从心。全球贸易体系受到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仅依赖4个参数来量化关税的全面效应,显然无法充分捕捉其复杂性。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大规模对等关税政策时,仅以如此简化的4个参数作为依据,未免太过轻率,难脱儿戏之嫌。
其次,USTR的“对等关税计算公式”中,双边贸易差额(xi-mi)较容易测算,Δτi测算的准确与否关键在于ε和φ的估算,而要想对这两个参数较为精准测算,需要大量微观数据支持,包括各国市场的需求结构、替代品可得性、消费者偏好以及行业间的异质性。例如,电子产品的价格弹性可能远高于农产品,而关税传递率(φ)在竞争性市场和垄断市场中差异显著。而USTR并未提供任何数据或方法论来支持其对ε和φ的估算,公式中的这些变量更像是形式化的符号,而非实际可操作的参数。
根据4月2日特朗普宣布的最终税率反推,USTR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忽略了上述变量的复杂性,将公式进一步简化为:Δτi=[(mi-xi)/mi]×0.5,并对其他贸易逆差比例低于10%的国家,大而化之地统一加征10%关税。白宫竟将这称为是对其他国家的“宽大处理”和总统的“仁慈”。上述简化操作抛弃了公式的理论基础,将其退化为一个鲜有经济学意义的简单算术运算,暴露了其伪科学本质。
在4月2日的发布会上,特朗普展示了一张由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递交的巨幅表格,表格中列出了各国对美国商品所征收的所谓“高额关税税率”。然而,深入分析后发现,这些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缺乏科学依据,很可能仅是通过将美国与各国的贸易逆差除以该国对美出口额得出的粗糙估算。
以印尼为例,表格显示其对美国商品征收64%的关税,但这一数字的计算过程可能是将美国对印尼的179亿美元贸易逆差除以其对美出口额280亿美元,直接得出64%。更令人费解的是,表格声称韩国对美国商品平均征收50%的关税,而事实上,《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自2012年3月15日生效以来,已将双边关税降至接近零,韩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如此高税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尽管美欧之间尚未正式签署全面自贸协定,但自2013年起,双方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及多项双边协议,已逐步将平均关税税率降至远低于10%的水平,特朗普所谓欧盟对美国关税高达39%的说法更是无从考证。
这种将贸易逆差比例直接等同于“关税税率”的做法,显然无法真实反映各国间的贸易壁垒。或许在某些个案中,价格弹性(ε)与关税传递率(φ)的乘积恰好为1,形成了巧合。然而,若多个国家的对等关税税率均与美国对其贸易逆差除以出口额的比值相吻合,则表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对等关税税率算法存在严重偏差。
事实的确如此。以2024年数据为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919亿美元,进口总额为4338亿美元,逆差除以进口总额得出67%(2919 ÷ 4338 = 0.6728),白宫再将此数字除以2,得出34%,这正是美国对中国的“对等”关税税率。同样的算法也适用于日本:202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为684亿美元,日本对美出口额为1482亿美元,相除后得出46%,再除以2即为24%,与表格中的对日关税税率一致。这种过于简化的计算方式,不仅缺乏经济理论支撑,更可能为全球贸易体系埋下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冲突隐患。
显然,USTR“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核心假设就是将双边贸易逆差直接等同于“贸易壁垒”,并以此推算对等关税税率。这一假设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缺乏根据。贸易逆差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受汇率、储蓄-投资差额、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非单纯由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决定。
例如,美国长期对华贸易逆差部分源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根据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国际收支恒等式,一国的贸易逆差(即净出口NX)在理论上近似等于国内总消费(C)与总储蓄(S)之差的负值,具体表现为NX=S-I(其中I为国内投资)。这一关系源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Y=C+I+G+NX(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G为政府支出),以及储蓄定义S=Y-C-G。代入后可得NX=S-I,表明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国内储蓄不足以覆盖投资需求的结果,需通过资本流入(即贸易逆差)来平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国际经济学理论中进一步指出,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变量(如储蓄率、投资需求和汇率)的结构性失衡,而非微观层面的贸易壁垒。因此,试图通过加征关税这一单一政策工具消除贸易逆差,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宏观经济驱动因素,无异于“缘木求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反而可能因关税引发的价格扭曲和报复性措施加剧经济效率损失。
第三,“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未考虑各国对美商品的非关税壁垒(如配额、监管措施)。不只如此,计算方法还忽略了汇率调整和一般均衡效应。加征关税可能导致美元升值,进而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Obstfeld, 1995)在《国际经济学》中指出,单边关税政策往往引发汇率波动和报复性措施,最终导致双输局面。特朗普的公式完全未考虑这些动态效应,其逻辑荒谬性显而易见。
第四,计算方法的政策目标设定不合理。从国际贸易理论看,“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加征关税实现双边贸易平衡(xi=mi),这在现代全球价值链(GVC)背景下很难实现。现代贸易中,中间产品跨境流动频繁,商品的生产过程涉及多个国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可能包含美国设计、但由日本制造的芯片,关税只会推高最终产品成本,伤害美国企业自身。在目前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关税的成本往往通过供应链传递,最终由进口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承担,而非出口国。这种复杂性使得“对等关税”计算方法的假设“通过关税简单减少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第五,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计算方法的设计和使用更多是政治工具,而非经济手段。特朗普通过宣称“对等关税”来塑造“公平贸易”形象,目的是迎合国内选民对“外国揩美国油”“占美国便宜”的不满,煽动国内保护主义情绪。这种看起来花哨的计算方法其实是在为强权政治、保护主义披上“科学”外衣,通过单边关税施压他国,迫使其他国家牺牲本国利益,放弃各国自主发展道路,顺从美国意志。
理论是推导结论的基础,若基础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无论形式多么精巧,最终结果都是错误的。失真的关税税率使得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失去合法性。
单边高关税冲击国际经济秩序
特朗普摒弃多边协商,挥舞单边关税大棒,试图通过高关税实现政策目标,这一基于错误计算方法的政策注定事与愿违。如果特朗普继续坚持,必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系造成深远冲击,同时威胁战后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引发各国报复性措施和加快全球贸易秩序重塑。
首先,反噬美国经济。加征对等关税的结果必然是“伤人一千,自损八百”,将对美国对外经贸关系造成严重打击。目前美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中间产品(如电子零部件)进口,关税将导致供应链混乱、生产成本上升及瓶颈问题加剧,高关税可能会削弱苹果、特斯拉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同时,若欧洲、中国、加拿大等对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猪肉)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出口将萎缩,中西部农业州经济受损,直接冲击特朗普的核心选民基础。
其次,各国报复引发WTO危机。面对美国单边关税,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国家声誉和尊严或作为谈判筹码,必然采取报复措施。
4月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接连发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欧盟与加拿大也已表态将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对美国发起反击。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加征“对等关税”未经WTO协商,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促使各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中方已就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对等关税”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起诉。若美国无视裁决(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惯例),WTO权威将进一步受损,各国可能转而依赖区域贸易协定,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碎片化加剧风险。
第三,冲击全球经济格局。当各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因“对等关税”萎缩,企业可能将供应链转移至那些未被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扫及的国家,短期内会令这些国家受益。然而,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成本高昂,效率损失显著,短期收益难以弥补长期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3%,但贸易战的升级可能导致这一数字小幅下调,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高关税政策还可能加速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特朗普对中国加征的不合理“对等关税”将使美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但也将削弱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促使中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2000年的70%下降至2024年的58%,贸易战可能加速这一趋势,长期来看或将动摇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
此外,加速区域经济整合。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不仅针对中国,还针对欧盟、加拿大等传统盟友。这种做法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加速区域性经济一体化,例如通过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来增强经济自主性。这种趋势不仅将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还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动摇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为美国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但其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冲击以及对美国自身的潜在反噬效应不容忽视。
结论与历史启示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计算方法在理论设计、数据应用和政策执行上充满谬误。基于这一错误计算方法实施的高关税政策不仅无法实现制造业回流、减少贸易逆差等目标,还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通胀、供应链混乱和出口萎缩的直接冲击。全球经济也将因贸易转移、美元地位受压和地缘政治紧张而承压。更严重的是,各国出于经济利益、国际声誉和主权尊严的考量,必然采取报复性措施,威胁以WTO为核心的战后多边贸易体系。
历史其实已经为特朗普加征关税引发的乱局给出了启示。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平均关税从40%提高到60%,引发全球贸易战,加剧大萧条。单边高关税不仅冲击经济,还可能重塑战后多边贸易秩序,带来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特朗普的单边“对等关税”政策看似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实则是在自戕。放眼未来,唯有回归多边协商,通过WTO框架解决贸易分歧,才能维护全球经济稳定,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余翔,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特约专家,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高级专家。文章仅为个人观点)
上一篇:烟台一女子烧纸祭祀引发山火,涉嫌失火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下一篇:基金投资必备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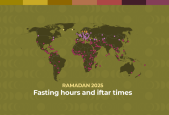







有话要说...